他是一名泽维尔男孩,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对澳大利亚伟大的阶级划分的第一次体验
他是一个泽维尔男孩。他的脸颊公平地闪耀着承诺和目标。
我曾去过他的学校一次。作为学校的辩论赛选手,我记得我被驱赶到了一望无际的车道上,来到主厅的圆顶豪宅,并认为它看起来就像《重访布莱德斯菲尔德》中的庄园。
他甚至有点像扮演注定要失败的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安东尼-安德鲁斯。作为一个小玩笑,我的泽维尔男孩甚至会随身携带一只泰迪熊。

我们走过墨尔本大学月光下的校园,当我们走到旧法律大楼的门廊下时,他紧贴着我。那是第一年,这是我的第一次大学爱情。
我对他说,我一直梦想着来到这里:在这所大学学习是我多年来努力的目标–而现在,看看我在哪里。
他用胳膊搂着我,在我耳边喃喃自语:”你真的做得很好,不是吗?”我可以感觉到我下巴下面的他的毛衣:它有一种光泽和一种我不明白的柔软。
显然,你可能被问到的最墨尔本的问题之一不是你在哪里买的咖啡,而是你在哪里上学。但我从来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
我想当你没有上过一所 “正确 “的学校时,答案根本不重要。他们仅仅通过看你就能知道吗?
我细心的哈维尔知道我来自哪里。


他认为我的学校听起来既古朴又狂野。他为我能进入这个具有地位和特权的地方感到真正的自豪,在这里我可以学习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史,而且一年级的医学生被告知他们是最优秀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在这里。
我坐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课程的第一年,一位年轻女士将我们正在讨论的乔托壁画的幻灯片投影图像与作品在现场的实际外观进行了比较–以及它在被清洗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她当时19岁,她去过帕多瓦。两次。
我觉得自己就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的样子。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巨大的阶级鸿沟。我从我们在学校比赛中辩论的私立学校的孩子们那里得到了一种模糊的势利眼,因为事实证明我们几乎是唯一参与的公立学校。
在与我这位优雅的新朋友一起在校园里转悠之前,我不认为我所取得的或即将取得的任何成就,除了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和未来的兴奋感之外,还有什么了不起。
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及这对他和我意味着什么。我已经把自己提升到了他的水平。我到达了他的羊绒般柔软的肩膀,以这种速度,我甚至可能属于他。
我们没能坚持多久。我和编辑学生报纸的那群人打成一片,他则沉浸在商业/法律中。我去参加了他的21岁生日,那是在一个游艇俱乐部举行的,他穿了一件晚礼服,他的母亲和妹妹穿着舞会礼服来到现场。
他最后经营着一个高知名度的企业。我们聊过一两次。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泽维尔学院的那个晚上,我在那里接受州辩论赛颁奖仪式上的最佳演讲奖。
但是,当我与我的老师和我的团队一起走上雄伟的台阶时,我们看到大楼里一片黑暗和安静。没有成群结队的人群。往里看,大楼是空的。
我们的辩论导师敲打着厚重的大门,一位看守人告诉我们,仪式在一周前举行。我们被告知了错误的日期。
我不记得自己有多不安,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的老师们的愤怒。他们带我们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吃晚饭,并坚持要求辩论协会的负责人到我们学校来,在集会上亲自给我颁奖。
对我来说,有人会故意把一个高中生排除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活动之外,这是没有道理的。我的老师们在一个资金不足、不受重视的国家系统中苦苦挣扎,却永远无法被说服。
本周末,”澳大利亚访谈 “将探讨阶级主义及其蔓延的假设如何在现代澳大利亚表现出来。而在周一晚上8点的ABC电视台,安娜贝尔-克拉布和纳泽姆-侯赛因将在我们的 “澳大利亚访谈 “特别节目中带领您了解澳大利亚人的整个心理和社会人事档案。
当我们从阿斯利康疫苗接种建议的新闻中回过神来时,及时提醒我们继续在飞行中建造这架飞机。在澳大利亚,对疫苗的犹豫是世界上第三高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不仅要更好地安抚,而且要让人们了解,如果我们不接种疫苗,澳大利亚将如何被抛在后面。
祝你周末安全愉快。苏格兰乐队Chvrches邀请The Cure的Robert Smith加入他们的新单曲,这是有推动力的独立流行音乐的完美组合,其中还夹杂着适量的怀旧情绪。
当口红碰撞在一起时–它是美丽的。
走好。
弗吉尼亚-特里奥里是ABC墨尔本广播电台晨间节目的主持人,也是ABC早餐新闻的前联合主持人。
首发于UNILINK官微 | 微信 AlexUnilink 电话 +61 2 8971 9963 | 提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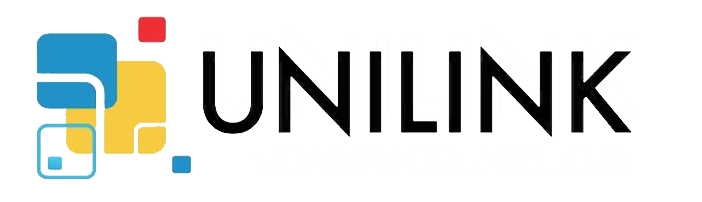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